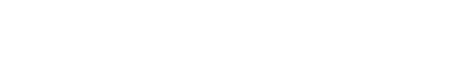百年前的登山打卡
《臺灣寫真大觀:山岳編》於1934(昭和9)年10月由臺灣寫真大觀社發行,攝影兼編輯者為桑子政彥。
乍看之下,讀者可能會以為,桑子政彥為某知名的山岳探險家與攝影家,在縱橫臺灣山林的同時,也以相機留下眼前震攝人心的自然之美。受過藝術史或攝影史訓練的讀者可能會進一步推論,本書必然是某種呈現「帝國凝視」的作品;就如同1938年來臺拍攝大屯山彙、新高阿里山與次高太魯閣三大國立公園的名攝影家岡田紅陽一般,桑子政彥必然透過他的鏡頭,以特定的構圖與取景,將當時被視為粗獷、野蠻、欠缺如日本內地一般對稱纖細之山型的臺灣山岳,收於方寸之間,再嵌入書頁中,添加適量的文字調味,成為都市人可安坐在室內,一邊啜飲著飲料,一邊逐頁品味的「目錄」。
我們也曾經如此想。然而,在查閱相關史料,釐清桑子政彥是誰,且試著從該書影像梳理出帝國視線及背後的意識形態,並檢視相片之材質、沖洗技巧與裝訂方式後,我們不得不得出這樣的結論:桑子政彥不是什麼名攝影家,甚至也不是本書主要的攝影者;任何嘗試從本書抽取某種一致之主題,乃至於主張此些主題為某種視線或意識型態之反映的企圖,將會是徒勞無功的。
為什麼我們會得出如此結論?讓我們先回答,在《臺灣寫真大觀:山岳編》出版的前後,臺灣的山岳中發生什麼事?
《臺灣寫真大觀:山岳編》發行時的1934年,由總督府殖產局山林課主導的森林計畫事業正步入尾聲。這個從1925年啟動、由受過近代林學訓練的林業官員,針對當時臺灣往往只能以「蕃地」或「官有林」籠統稱之的臺灣森林,將當中應由政府保存者劃為「要存置林野」,其餘則歸為不要存置林野。在前者中,林業官員再基於原住民治理、林地之多目標利用等考量,另外畫出「準要存置林野」,即「以要存置林野為準來辦理」之意。1931年,前述區分調查的成果初成;總計劃出要存置林野1,094,619.1732公頃,準要存置林野200,072.3500公頃與不要存置林野77,212.8020公頃,合計1,371,904.3252公頃。針對要存置林野,林業部門再將之細分為29個事業區,每個事業區並搭配一本「施業案」,列明未來20年之林業永續經營的規劃。在臺灣林業史上,森林計畫事業為重大里程碑。事實上,要存置林野即為今日的國有林班地,準要存置林野為原住民保留地,不要存置林野則常為糖廠、農場的土地。在此近代林業之藍圖逐步完備後,再加上日本帝國進入戰時體制,對木材的需求日增,臺灣林業也進入集約經營的時代,伐木與造林的強度攀上史無前例的高峰。證諸日治時期的林業統計資料,臺灣的用材生產於1927年超過100萬石(28萬立方公尺),11年後(1938)才倍增至200萬石(56萬立方公尺),但翌年(1939年)的用材產量旋即突破300萬石(84萬立方公尺)。林業躍升為臺灣軍需工業化的急先鋒。[1]
1920年代的總督府關切的不只是森林之永續利用而已。事實上,總督府之所以決定於1925年啟動森林計畫事業,很大原因來自於對既有林業政策的反省,並探索伐木以外的森林利用方式。就拿總督府投注莫大心力開發的阿里山林場為例。1904年,面對號稱「無盡藏」的阿里山森林,總督府決議移植當時最新進的伐木集材設施,特別是美國西北太平洋以鐵路為主軸的經營模式,以求有效率且永續地砍伐這片帝國境內絕無僅有的原始林,並以井然有致的人工林取代之。至1920年代末期,隨著阿里山鐵道沿線的原始林逐步消失,社會上逐步出現「保育」阿里山之天然景緻的呼聲。對此,林業官員也相當為難;他們認可景觀保育的重要性,但鐵道的營運成本過於龐大,如不持續伐木挹注,恐怕阿里山林場將無以為繼。就在此時,林業官員注意到,有越來越多的觀光客搭乘鐵路上山,或則親炙阿里山林場各類規模宏大的基礎設施,或則持續深入,探索臺灣最為「原始」的心臟地帶。林業部門開始構思以觀光為鐵道續命的可能性。且此見解正與日本帝國國策合拍。1931年,日本政府頒行〈國立公園法〉與設立判準,開始積極籌設國立公園。國立公園即為national park,以1872年的美國黃石國立公園為濫觴。依據日本國立公園協會的見解,只有那些「造物者」偶然創造的大風景方可被劃入國立公園,一方面可為帝國臣民所「鑑賞」,從中得到性靈之提升,另方面可吸引外客,為當時困窘的帝國財政帶來外匯。1933年,總督府成立臺灣國立公園調查會,翌年指定新高阿里山、次高太魯閣與大屯山彙指定為「國立公園候補地」。1937年12月,總督府正式公告三處候補地為國立公園。即便在臺灣進入戰時體制後,「國立公園」一詞因其與「美帝」、遊樂間的連結而遭到棄卻;但原先被劃入國立公園的地域,因其能健強體魄、培養人民之愛國心,成為帝國臣民之養成所。
不管是森林計畫事業還是國立公園,意味著總督府對昔日位於番地、相當於臺灣原始、粗獷與野蠻性格之代表的山岳,在知識的累積與控制手段上,已臻新的高度。與前述趨勢相輔相成者便是「近代登山」風氣的興起。日治時期臺灣著名的登山家沼井鐵太郎便表示,臺灣登山史可分為史前期及初期探險時代、開拓探險時代、探險登山時代與近代登山時代。他認為,1920年代中葉,隨著臺灣山岳會等登山團體的成立,原本由政府與學術界主導,登山只為資源調查與地理探勘之手段的「探險登山」逐步走入尾聲,相對純粹的、「為登山而登山」的「近代登山」,曙光乍現。沼井寫道:
「此時代的初登紀錄開始由官憲及學術調查以外的純粹登山者所建立。尤其是大霸尖山的首次登頂,當初是由臺灣山岳會一手創造,是人類史的初登,為臺灣高漲的登山意識提供劃時代的原動力。此後臺灣的登山趨勢是對未知高山努力開路初登與紀錄,憑藉自力挺身於山岳高難度路線的初次攀登。勇氣與野心成為一般登山家的登山動機。」[2]
《臺灣寫真大觀:山岳篇》即是在此脈絡中誕生。《臺灣登山小史》記載,「1932年7月,由佐佐木舜一擔任領隊,河南宏、清水善次郎、古平勝三、桑子政彥、山河友次、荻坂剛等人所組成的大霸尖山、次高山植物調查、寫真攝影的專門研究登山」。[3]《臺灣山岳彙報》則記載了此專門研究的後續:
「前前號預告原本的時間將延期至9月24日(六),但就在活動要開始的前一刻,原本預定地會場卻無法使用,因此只能急忙變更至台北商業學校雨天操場。上述內容並未在報紙上刊載,主要是因為時間為新聞社的放假時間,及其他地方也有許多種的展覽的關係,因此並未達到一開始所期望的盛會。」
當日展覽會出品物為佐佐木舜一氏所收藏之大霸尖山、次高山的植物蠟葉標本107種;河南宏氏同樣是大霸尖山及次高山的植物蠟葉標本87種,及日本阿爾卑斯山的植物蠟葉標本37種;島田彌市氏的日本阿爾卑斯山植物蠟葉標本51種;古平勝三氏所收藏的珍奇蛇類標本3種;見元了氏所收集之台灣五岳(新高山、次高山、南湖大山、大霸尖山及大武山)的照片(全紙);河南氏所收藏之大霸尖山、次高山方面的照片(半藏20張,手札68張);桑子政彥氏的能高山、次高山、大霸尖山等的照片(全紙)4種;台灣寫真大觀社的小林氏所提供之台灣山岳各地照片40種;台北高等學校所提供之大霸尖山、次高山連峰的大寫生素描圖2種;佐佐木氏所提供同方面的地圖1種。不論哪一種皆是美事一樁,讓觀賞者可以有身入其境之感。
下午3點半左右則由佐佐木氏以「大霸尖山、次高山的縱走及植物帶」為題進行演講。與會者皆是對於山及植物有所熱情之人,因此很認真地聽著發表人的觀察、經驗及其結論,演講於下午4點半結束。之後彼此針對展覽物提出相關詢問、討論及閒聊,因展覽預計5點結束的關係,因此帶著一點遺憾地落幕。
在展覽的最後對於當日爽快出借場地的台北商業學校,照例給了十張美麗的海報,作為田口與四郎、演講者、出品者併會員們滿腔的感謝。
當日與會者為鈴木、堀川、佐佐木、島田、古平、沼井、土肥、小林、財津、大橋準一郎、山本、河南、山河、桑子、山村、齋藤齋、伊藤鐵兒、木田氏等諸會員,加上非會員者合計40名左右。[4]
似乎可以推測,《臺灣寫真大觀:山岳編》為此次「專門研究」的成果之一。從前述報導,我們幾乎可以想像,數十名鍾情臺灣山岳的登山者,在一字排開的植物標本與相片前,交換植物採集與攝影的心得,然後端坐著聆聽佐佐木舜一對高山植物分佈的看法。佐佐木舜一為林業官員,長期投入臺灣高山植物相的調查與研究。他最感興趣的主題就是臺灣植物相與周邊地區的比較研究,致力發掘臺灣在生物地理學的地位。即便此聚會看似盛況空前,兼具學術與娛樂性,但從報導也可看出,籌辦此次聚會的臺灣山岳會,對於臨時改地點,讓不少隊登山與攝影懷有熱情的愛好者向隅,不甚滿意。是否因為如此,與會者決定編纂攝影集以饗同好?讓當天未能到場或撲空的登山攝影愛好者多少能共襄盛舉?史料無法回答前述問題。要回答《臺灣寫真大觀:山岳編》究竟為何與為誰編纂,我們得另闢蹊徑。
本展覽的另一策展人李旭彬為攝影史研究者與攝影師。在收到國家攝影中心寄來、已數位化之《臺灣寫真大觀:山岳編》後,除了在螢幕上細究每張照片之構圖等細節外,他決定至國家攝影中心的典藏庫,親眼檢視該書的「物質性」。以下為其現場報導:
「本書為橫式右翻,右側兩孔穿線裝訂。封面由3至4公釐灰色厚紙板糊豬肝色仿皮紋圖樣封面紙組成,標題為手寫毛筆字體並燙金處理。內頁為一公釐的黑色霧面卡紙,影像為手工銀鹽相紙,說明文字為打字後裁切的字條,兩者皆以膠水黏貼固定在黑色卡紙上。
再就影像本身而論,本書影像尺寸共有兩種,一為約16.5mm x 12mm,另一種為長形27.8mm x 11.4 mm。以放大鏡檢視,其銀粒子排列非常緊密,應無經過放大機投影放相,且當時以膠基底片經放大機放相尚不普遍。此外,相紙上大部分的明膠皆已黃化,影像的四周局部多已出現老照片特有的銀粒子析出現象,且相紙本身無法明顯判別是否有現代相紙的硫酸鋇塗層。由以上線索,可以推測多數影像皆為當時所流行的 5”x7” 乾板玻璃底片所拍攝,並使用印樣箱進行接觸印相(Contact Print)之法印製。另一個長形尺寸的照片,推測為 8”x10”乾板玻璃底片,並將底片夾的遮片沿長邊裁半,使得一張底片上可以拍攝兩張 4”x10” 的影像,再經由印樣箱再進行印製。」
他的結論為,《臺灣寫真大觀:山岳篇》並非由出版社大量發行的攝影集;或許是桑子政彥本人,又或者是他的助手或朋友,逐張印出每張照片後,黏貼至卡紙上,再裁下圖說的紙片,貼在照片周圍。每本《臺灣寫真大觀:山岳篇》都是獨一無二的存在。
我們決定把《臺灣寫真大觀:山岳篇》稱為百年前的登山打卡。為什麼是打卡?打開各位的臉書或IG,隨意瀏覽幾張打卡照。打卡有到此一遊之意;至於「一遊」的地點,往往是口耳相傳、不容錯過的景點。然而,我們應該也可以體會,打卡照並不簡單;在可能有數萬人曾經打卡過的景點前,且觀看者可以各種hashtag搜索與比較時,打卡照得展露打卡者不被框架所限的巧思與創意,方能吸引眼球。或許可以這麼說,打卡的精神是「沿著軌道出軌」又或者「循著常規地挑戰常規」。
這便是我們在逐頁審視《臺灣寫真大觀:山岳篇》時體會到的精神。在本書收錄的照片中,讀者既可看到大屯山、新高山、大霸尖山等當時臺灣的名山,乃至於眺望這些名山的標準角度;與之同時,我們也可看到如霧頭山這樣相對少為人知的山岳,以及「由下而上地仰望」此深具實驗性的攝影視角。在主題方面,本書既呈現雲海、山頂眺望等相對典型的風景,同時也收錄意圖描繪高山植物生態、原住民日常生活、登山過程等較為少見的影像。如前所述,我們一度為本書的多樣性而目眩神迷,同時也為本書究竟要傳達什麼訊息,感到困惑。不過,經過一番抽絲剝繭後,我們認為,如此難以歸類的特性便是本書最大特色。追根究底,《臺灣寫真大觀:山岳編》是一群攝影愛好者,在花費大筆積蓄購得相機後,興致高昂地「外拍」,針對彼此的作品品頭論足後,意猶未盡地製作了紀念專輯,為此一期一會做紀念。本書面對的不會是數量眾多、面貌模糊的「大眾」;它是手工製成的紀念品或同人誌,又或者是維繫臺灣登山社群的禮物。
取名為「百年前的登山打卡」還有另層意義。為什麼現代人熱衷打卡?這或許牽涉到,在這個瞬息萬變的世界裡,人們還是期待以某種形式留下吉光片羽,乃至於曾在此吉光片羽中活過的自己。回到百年前的臺灣。是什麼驅使登山者按下快門?這或許也牽涉到,當森林計畫事業預示了臺灣山林的進一步開發,而國立公園之設置顯示登山遲早會成為臺灣社會日常生活的一部分,登山者期待以相片留下這即將消逝的原始與粗獷,以及那種「山在那兒、便朝著山走去」的野心、好奇與勇氣。曾於1928年至新高阿里山探勘、評估於該處設置國立公園之可行性的田村剛,當站在萬歲山上,身邊郡役所職員喋喋不休地說明阿里山開發的未來計畫時,默默地拍了照片,並在筆記上寫下:「我決定盡快用相機將這景觀給記錄下來,至少在這個計畫成真後還能夠保有原始的景色。我與那些役所的人不同,我希望以後都可以守護著南方的那片樹海」。[5]
*本文得以完成,要感謝407林業部成員李翊媗、謝宜彊、張雅綿協助尋找與翻譯史料。我們也要感謝國家攝影文化中心,給我們充分的時間與彈性,完成所需的研究後,再著手撰寫此篇導論。
[1] 關於森林計畫事業的始末及其對臺灣森林開發的影響,見洪廣冀,〈從「臺灣之恥」到「發展最速的產業」:再思日治時期臺灣的科學林業與工業化〉,《臺灣史研究》25卷3期(2018年9月),頁83–140;洪廣冀、羅文君,胡忠正,〈從「本島森林的主人翁」到「在自己的土地上流浪」:臺灣森林計畫事業區分調查的再思考(1925–1935)〉,《臺灣史研究》26卷2期 (2019年6月),頁43-111。
[2] 沼井鐵太郎著,吳永華譯,《臺灣登山小史》(臺中市:晨星,1997),頁99-100。
[3] 沼井鐵太郎著,吳永華譯,《臺灣登山小史》,頁183。
[4] 〈山に關する植物標本と山岳寫真の展覽會及講演會〉,《臺灣山岳彙報》第4卷11號(1932年11月),頁54。
[5] 田村剛,《臺灣の風景》(東京:雄山閣,1928),頁11-12。